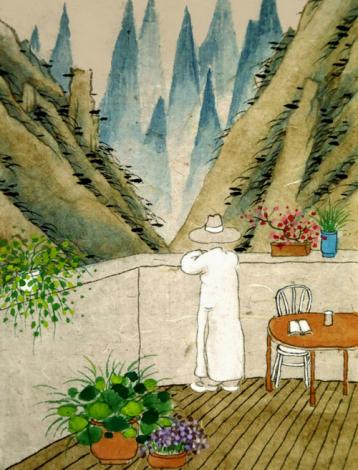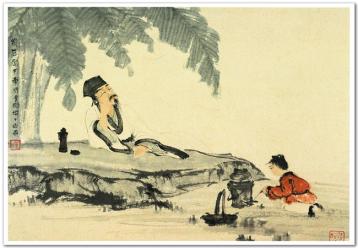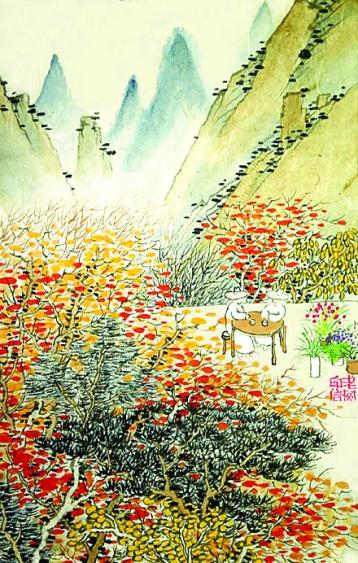周作人的“苦茶诗”
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
只欠工夫吃讲茶。
这两首诗写得既庄重又诙谐,既写实又含蓄。第一首的尾联“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是全诗的总结。1965年12月周作人在给香港报人潘耀明的回信中,谈到对此句的说明。他写道:“打油诗本来不足深究,只是末句本来有个典故,而中国人大抵不懂得,因为这是出在漱石(即日本知名作家夏目漱石——引者注)之《猫》里面,恐怕在卷下吧,苦沙弥得到从巢鸭风俗院里的‘天道公平’来信,大为佩服,其尾一句,则为‘御茶ごきめがれ’,此即是请到寒斋吃苦茶的原典也。”其实,周作人的这两首诗反映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对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社会动荡,他本人无能为力,只得退避三舍,逃避现实,消极出世,以收藏、农耕和饮茶为乐,以便排解其郁闷的胸怀。因此,饮苦茶,就成了他排解苦闷的象征。因此,诗的末句“请到寒斋吃苦茶”,就成了读他的散文时,理解其内涵的一个先导,尝尝“苦茶”的味道,就能帮助读者理解他的散文的内涵。当时周作人这两首诗在林语堂主编的《人世间》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有的推崇,有的批判,在文坛上颇为热闹了一番。
根据他在《喝茶》一文的自述,他最喜欢喝绿茶,对外国人喝的加糖与牛奶的红茶,从来不感兴趣。他说:“我的所谓喝茶,确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他平日饮茶就“像是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大口大口地喝。看来似乎不太讲究,但是对饮茶的环境及用具还是很讲究的。特别是在邀请朋友一起饮茶时,一般是要在“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尘梦”。他认为喝茶时不要吃瓜子,所吃的东西应以清淡的“茶食”,如,“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还有“各色‘羊羹’”,尤有特殊的风味。再就是江南茶馆的豆腐干切成的细丝,亦颇与茶相宜。
在20世纪60年代他为香港《新晚报》写的《吃茶》一文中谈到他吃茶是够不上什么品位的,从量与质来说都够不上标准:“从前东坡说饮酒饮湿,我的吃茶就和饮湿相去不远。据书上的记述,似乎古人所饮的分量都是很多,唐人所说喝过七碗觉腋下习习风生,这碗似乎不是很小的,所以六朝时人说是‘水厄’。我所喝的只是一碗罢了,而且他们那时加入盐姜所煮的茶也没有尝过,不晓得是什么滋味,或者多少像是小时候所喝的伤风药午时茶吧。讲到质,我根本不讲究什么茶叶,反正就只是绿茶罢了,普通就是龙井一种,什么有名的罗岕,看都没有看见过,怎么够得上说吃茶呢?”
周作人从小就喜欢喝家乡的一种叫做“本山”的茶,后来这种茶改名为“平水珠茶”,可是在北方买不到,只得买龙井喝。但是所能买到的也是普通的种类,若是旗枪雀舌之类却从没有见过,碰运气可以在市上买到碧螺春,不过那是很难得遇见的。他“就是不喜欢北京人所喝的‘香片’,这不但香无可取,就是茶味也有说不出的一股甜熟的味道”。 
周作人的“苦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