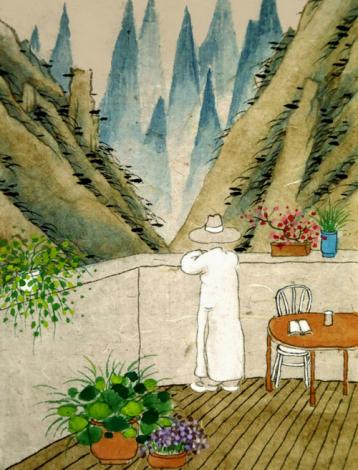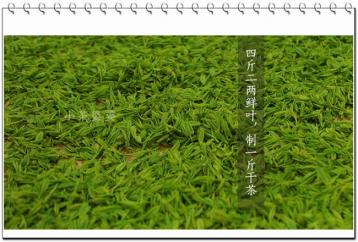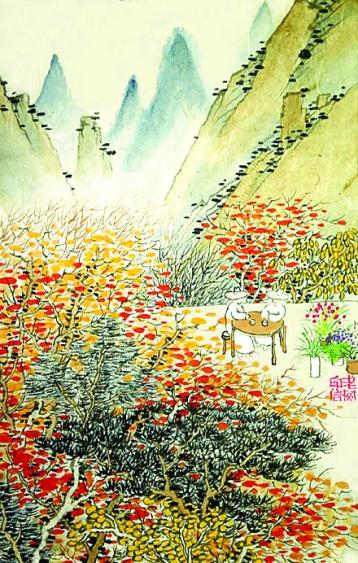论宋代皇帝的茶诗|饮茶诗鉴赏
本身就具有一种超然物外、接纳自然的态度,并象征着性情的高雅和对自然的崇尚。
品茶人并不是用茶水来解渴,更不是用茶来消磨生命,而是在品茶的过程里,体会着庄子所言的“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的静神为美、静神为养的养生之道。故宋高宗赵构云:“久坐方知春昼长,静中心地自清凉”,就是这种“虚”与“静”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2、茶中有禅
在古人眼里,茶树与草药都为有灵性的植物,《东溪试茶录》有云:“茶于草木为灵最矣”;陆羽《茶经・茶之源》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从来佳茗似佳人”,“不是膏油首面新”。茶君子们称茶为“香芽”、“金芽”、“灵芽”、“灵草”、“瑞草”等,因此,品茶之事常与神仙、道士等隐居者联系在一起。
品茶中品味天地之奥妙,品茶中陶冶内在之灵性,成了饮茶人的一种玄机。在幽香而清淡的茶味里,在似梦似真的冥想中,在若有若无的清风里,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功名利禄化成了一场云烟,人间烦忧成了一缕空气,茶里有了天地大化的禅机。
正如冯文开所讲:“独饮是在孤独中体味茶的神韵,由茶及己。对嚷是在对话、轻言、密语、谈私中进入茶的胜境,体会饮茶的情趣;聚饮是在活泼、畅怀、舒啸中得到品茶的乐趣。茶中之禅浸透了文士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乃至行为方式。文士在茶中致力于获得心灵的超越,在茶境中追求适意。文士饮茶一面看出他们委顺于世、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一面在茶中得到空静澄明、了无挂碍、人生空幻的禅悦之境。
另外,他们在缕缕情香中获得一种安之若素、处之泰然、超然平淡的心态,一种逍遥闲适之情趣。”所以,宋太宗赵匡义的“鹤唳九宵堪入画,云平三界化无私。真宗相教非虚说,对境成空是我师”表现的正是这种茶中所包含的禅机。伴随着茶香,不知不觉之中,饮茶人的心灵已登临三界,与仙人为伍,与天地遨游,此情此景,正如朱熹《茶灶》诗所言:“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3、茶中有精神
唐代诗僧皎然有《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徒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
这首诗俗称“七碗茶”诗,是说饮茶可以荡涤人的烦忧,使人精神爽朗,产生如飞雨洒轻尘之轻快感。从客观效果来看,饮茶确实有提神醒脑之功用,又可以温胃养肝,净化人的血液,所以长期饮茶能使人心绪宁静,身体通透,精神振作,四肢轻松。
因此陆羽《茶经》中引壶居士《食忌》言曰“苦茶久食羽化”,又引陶弘景《杂录》云“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都说明饮茶通过优化身体条件,从而达到静化精神的作用。因此,茶就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成了一种古朴宁静、优美空灵的自然世界的具体物质,故饮茶才在宋代文人中蔚然成风,也成了文人间联络感情、沟通心灵的最佳方式,即使贵为天子的宋徽宗赵佶也要以茶为宴,亲为大臣烹茶而一展茶技,从而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综上所述,乃知品茶是人生之大美,茶道是自然之精华与人类自身的一种高雅的契合,茶诗正是这种大美之道的具体写照,它融合了茶的芬芳与诗的高雅,更有一种别样的情趣在其中。宋代皇帝们深谙茶道,又拥有天下茶之极品,所以他们完全有理由借茶悟道,借茶抒情,借茶诗来表现他们独特的人生感受了。
参考文献:
[1] (唐)陆羽:《茶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叶羽:《中国茶诗经典集萃》,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
[4] 冯文开:《北宋茶诗与文人情趣》,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5] 蔡镇楚:《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6] 余悦:《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作者简介:周利,女,1952―,河南南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汉语,工作单位:河南中医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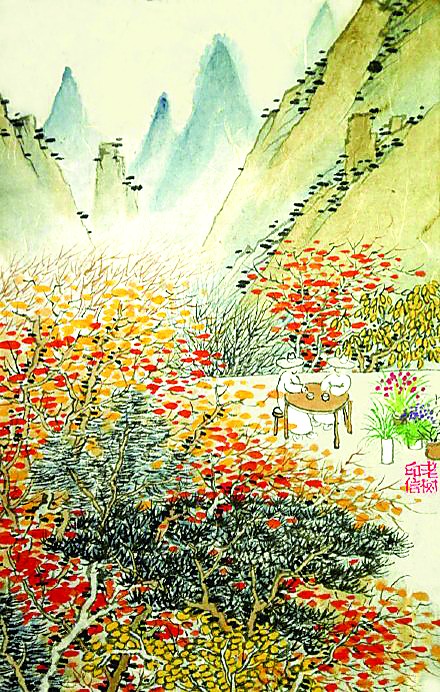
论宋代皇帝的茶诗
饮茶诗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