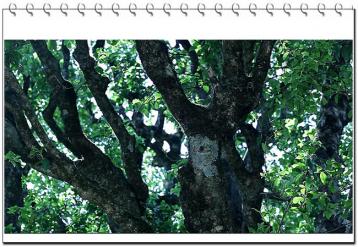中俄茶文化差异比较谈|俄罗斯茶文化
sp;
而俄罗斯仅有南部的索契出产少量茶叶,因此主要依靠进口,中国的种茶、采茶、制茶、烹茶、品茶文化没有随茶叶一同传人俄罗斯,与日本不同,早期俄罗斯人得到茶的途径并非由本国人带回。
公元1618年,明万历46年,派钦差大臣访问俄罗斯,经18个月到达莫斯科,携带礼物中有4箱茶叶,赠给俄皇。公元1727年,清雍正5年,中俄签订《恰克图互市界约》,晋商将茶叶运此与俄商贸易。
最初因数量有限,交通不便,茶最初是俄罗斯贵族的奢侈消费品,功能是用来醒脑、活血和提神。但19世纪很快就普及到民间。与中国的感性思维不同,俄罗斯人并没有赋予茶太多的理想色彩,而是将之作为正餐外的佐餐,配合各种小食品,作为休憩时能量的补充、用于时光的消闲。按照饮食结构来说,俄罗斯人嗜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品,且品种单一,饮茶能够有效地预防相关疾病,以其健康属性为俄罗斯大众所接受。那些看起来玄而又玄的茶道精神,似乎与热情、乐观的俄罗斯人并不搭界。
二、饮茶方式——忆苦与思甜
中国受《易经》、《老子》的影响,较早便形成了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如阴阳转化、福祸相依、否极泰来的思想,使中国人对生活常持辩证思维,加上佛教所言之“苦谛”说(即“世界上一切皆苦,人生无事不苦”)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人一种特有的人生观,即细品人生苦难,较少彻底绝望,亦少绝对乐观。对于“苦”他们有深刻地感悟,加之五行观念的影响,使得中国人将食品也分为五味:酸、甜、苦、辣、咸。而茶则属苦。
《神农本草》:“茶味苦,饮之使^益思、少卧、轻身、明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茶苦而寒……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将则上清矣”。 对苦的认可,对清的追求,对茶性的认识,使中国饮茶也经历了一个由掺杂葱姜调料到添盐末最终改饮清茶的过程。宋人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盐……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当时人们发明了蒸青散茶制法,不用碾成末、也不用盐调味,重视茶叶原有之香,大概就是为了更好地品茶之真味,感悟微苦人生之回甘。
而俄罗斯人则恰恰不同。除地理因素外,俄罗斯人喜甜食,巧克力、糖果都甜腻得过分,在茶引入俄罗斯之前,俄罗斯人喝一种热蜜水的饮料,即水加蜜糖、香料和草药制成的热饮,并且有配套的蜜水壶。茶引入之后,除了有时在茶中直接加入砂糖、蜂蜜、柠檬片之外,他们更是为茶配备了大量的甜点,如奶渣饼、蛋糕、饼干、糖果、果酱等等。俄罗斯用来感谢主人招待的俗语“谢谢糖茶”更是体现了糖茶的密不可分。
相对于中国对饮茶程序的繁复要求,俄罗斯人是豪放而朴实的,他们可以用茶碟喝茶,即把茶倒入小茶碟,双手平放托着茶碟,口中含上一勺蜜,再一小口一小口的啜饮着茶。或是用以糖伴茶,看糖喝茶,他们沉浸于现实生活的片刻享受,使得俄罗斯人保持着乐观的品格。中国人喜欢借茶消愁,如“三饮便得道,何必静心破烦恼’”,但仍旧建立在破愁之上,不若俄罗斯人无愁之干脆。正所谓一个善忆苦,一个喜思甜。
三、饮茶器物――炽热金属与温润陶瓷
俄罗斯人的茶炊非常讲究。俄罗斯人有“无茶炊不能算饮茶”之说。俄罗斯的茶炊多为铜制,配以精美华丽的外装饰,行如中国的火锅和大铜茶壶,内有炊膛,外有水龙头和把手,下有炉圈和通风。可用松明、煤油和电加热。好的茶炊成为家庭工艺品,逐渐成为“礼器”,平时用电茶壶,只有在节日和聚会时,传统的茶炊才会被拿出来使用。著名的俄罗斯作家普希金有诗专门描述这一场景:
天色转黑。晚茶的茶炊
闪闪发亮,在桌上咝咝响。
它烫着瓷壶里的茶水:
薄薄的水雾在四周荡漾。
这时已经从奥尔加的手下
斟出了一杯又一杯的香茶,
浓酽的茶叶在不停地流淌
这与俄罗斯金属制品技术成熟关系密切。精巧的俄罗斯手工艺者在钢铁上雕刻美丽的花纹,使得俄罗斯器皿实用而华美,多为铜器。那种热得快、凉得快干脆利落的方式颇为风风火火。
而中国往往以陶瓷为主,苏东坡说“铜腥铁涩不宜泉”,“定州花瓷琢红玉”。认为用铜器铁壶煮水有腥气涩味,用石制锅具烧水最佳;喝茶最好用定窑兔毛花瓷。中国用来饮茶的茶具以紫砂为多,大概是农业文明对于土地的天生亲昵,偏好温润而天成的陶器和瓷器,这与中国的烧陶冶土技艺发达有关,其中也包含了中国的五行思想,以土养茶,温润而厚重,颇为稳重有君子之风。 
中俄茶文化差异比较谈
俄罗斯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