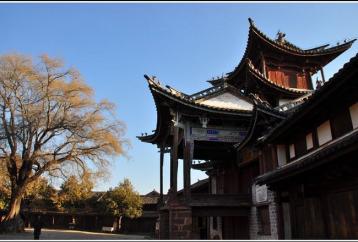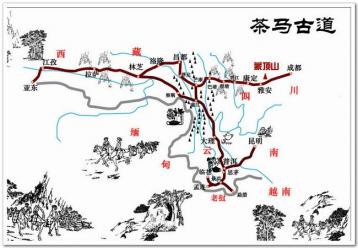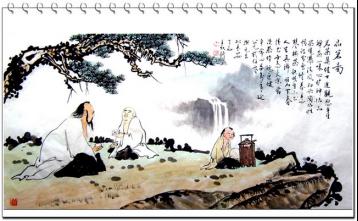历史上的五大著名茶人
看尽人世沧桑之后,惟独对茶的喜好未曾稍减。其实,他在感叹宦海沉浮、人生坎坷的同时,也表露了自己一生爱茶的嗜好。
综观历史与现实,我们在高度评价欧阳修在文学、历史、政治等方面的杰出成就时,也不能忽略他在品茶、诗茶、兴茶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苏轼品茶追求“静中无求,虚中不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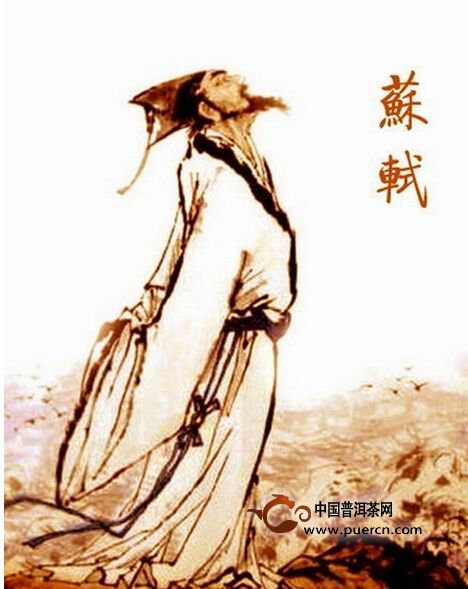
在中国文坛,有“李白如酒,苏轼如茶”之喻。李白的诗歌豪放飘逸,充满了酒神般的浪漫、洒脱,苏轼的诗词豪放内敛,体现了沉稳与理性,犹如茶的淡雅清高之特性。李白仕途虽有波折,但出生在大唐盛世,身心总体愉悦。而苏轼的为官生涯一直处在朝廷变革期,并成为新政之争的牺牲品,身心疲惫,感慨良多。
正因如此,苏轼没有选择像李白那样寄情山水,而是忧国忧民,寄情茶道。他把茶比为“佳人”、“仙草”、“志向”,视茶为自己的好友。他通过品茶来体悟人生、感知玄理,并努力从中寻求心灵的解脱。这也成就了苏轼茶香四溢的传奇一生。正如后人所评价:“读苏轼诗文,染茶味清香。”
作为宋代大文豪,苏轼一生创作了多篇关注现实、关爱民生、抒发情怀的佳作。其中,苏轼的咏茶诗尽情表露了其超凡脱俗的旷达情怀。有研究者总结,这种旷达情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追求清淡闲适的生活;二是表达以茶会友的真情;三是寄寓以茶养生的情趣;四是抒发失意遣愁的人生感慨。比如,《水调歌头》云:“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该词绘声绘色地记咏了采茶、制茶、点茶、品茶全过程。又如《西江月》云:“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该词细腻传神地描绘了茶水的形态,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品茶过程的美妙感受。
苏轼不仅以诗词名闻天下,而且还精通茶道。他认为,品茶的最高心境是“静中无求,虚中不留。”他在品茶中讲究心境和虚静,写出豪放柔美的诗词,比如“人有悲欢离合,月由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天宇之间发出了自己的呼喊,让心灵随着感悟进入了无限的时空之中。
苏轼品茶,对茶友和茶具有较高的要求和品位,正如在《扬州石塔试茶》中写道“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他对茶的养生作用也十分注重,正如在《物类相感志》中写道:“吃茶多腹胀,以醋解之。”此外,他还用陈茶驱蚊虫。每当夏季,他都会把陈茶点燃,然后吹灭,以茶烟驱蚊虫。苏轼对煮水的器具和茶具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谪居宜兴蜀山讲学时,提出“饮茶三绝”之说,即茶美、水美、壶美,惟宜兴兼备三者。他认为“铜腥铁涩不宜泉”,泡茶最好用石烧水。
俗话说:“水为茶之母,壶是茶之父。”苏轼在宜兴时,还亲自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烹茶审味,怡然自得,题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与此同时,苏轼还自创了一套“苏氏饮茶法”:每餐后,以浓茶漱口,口中烦腻既去,牙齿也得以日渐坚密。用中下茶漱口,而上等好茶不易得,“间数日一啜,亦不为害也”。
即便倡导“静中无求,虚中不留”,苏轼与文人骚客之间的斗茶斗才算得上宋代茶文化的一大亮点。一天,苏东坡、司马光等一批文豪斗茶取乐,苏轼的白茶取胜,心里乐滋滋。看到茶汤尚白,司马光便有意为难苏轼说:“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同时爱此二物?”苏轼想了想,从容地回答:“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司马光问得妙,苏轼答得巧妙,众人称赞不已。
苏轼的一生,足迹遍及全国多地,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南,从峨眉之巅到钱塘之滨。长期的贬谪生活不仅为他提供了品尝各地名茶的机会,也让他在沉苦之时一度保持着激扬澎湃的宽阔胸怀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如果说人生是一杯茶,那么泡这杯茶、品这杯茶、评这杯茶的主角恰恰就是我们自己。苏轼的这杯以“静中无求,虚中不留”为主题的生命之茶因为其人生历练和文学创作而泡出了独特的诗意芬芳,日久弥香。

在中国人心中,茶占有独特的地位。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话题都可以与茶相关,因为茶可以雅俗共赏,也可谓老少皆宜。把日常趣事与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写进诗词中,这绝对是一件有文化、有品位的事。南宋大诗人陆游就是这样一位茶客。陆游一生,是与诗、词、文、书、茶、酒、琴相伴的,而茶为尤甚。陆游用大量篇幅咏茶与诗词、茶与书法、茶与琴棋、茶与友情以及茶事活动,被后人喻为“重谱茶经又一篇”。
据统计,《陆游全集》中涉及茶事的诗词达320首之多,是历代创作茶事诗词最多的诗人。在这320首茶诗词之中,有100多首是吟颂建茶的。这主要源于陆游曾任福建路常平茶事、三主武夷山冲佑观等茶官职务,主管建茶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陆游又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建茶诗人。
陆游爱茶、嗜茶,胜过酒。在酒与茶的选择上,陆游有着鲜明的态度:“难从陆羽 毁茶论,宁和陶潜止酒诗。”换言之,他可以不喝酒,而茶却不能缺少。
早在汉代,便有“建溪芽”。唐代茶圣陆羽 的《茶经》见证了建茶之名。《茶经》写道,建州之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唐末已成为贡品。到了宋代,建茶成为当朝时尚,便常见之于诗文之间。
一生寄深情于茶的陆游对建茶一向倾慕。隆兴元年(1163年),陆游从福建宁德主簿任满回临安,受孝宗皇帝赐进士封号,任枢蜜院编修,获赐“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的北苑龙团凤饼茶。小饼龙团是福建转运使蔡襄督造入贡的“上品龙茶”,专供皇帝使用或恩赐的御茶。对此,陆游在《饭店碾茶戏作》中赞誉建茶:“江风吹雨喑衡门,手碾新芽破睡昏。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溪村”。这是陆游与建茶结缘的开始。
自古以来,赞颂建茶、建盏、建安斗茶的诗文数量之多、名家之齐,堪称中国文坛一绝。其中,陆游的《建安雪》把建茶描绘到了极致。该诗云:“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小雪。雪飞一片茶不忧,何况蔽空如舞鸥。银瓶铜碾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荔子腴玉肤,自古难兼熊掌鱼。”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作为“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的专职官员,陆游初到建安时,看到春雪纷飞,便联想茶叶丰收的征兆,高兴地写下此诗。对于建茶的韵味,陆游曾有过多种描述:“舌根茶味永”,“茶甘半新啜”,“瓯聚茶香爽齿开”和“茶散茶甘留舌本”等赞誉建茶的高贵品质。
除了诗茶外,陆游对茶的烹饮之道非常在行。他总是自己动手烹煮,并以此为乐,常年坚持。如何掌握煎饮的火候?他曾对“效蜀人煎茶法”和“忘怀录中法”做了深入研究,其创作的《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北岩采茶用<忘怀录>中法煎饮,欣然忘病之未去也》等诗中足以佐证。
在古代,分茶又称茶百戏、汤戏、或茶戏。它指的是在沏茶时,使茶汤的纹脉形成不同物象,有的如山水云雾,有的似花鸟虫鱼,有的像画图和书法。只有具有很高的烹茶技艺者,才能从分茶中获得游戏的情趣。陆游对分茶情有独钟。他在江西临川和浙江杭州为官的那些日子里,特别喜欢分茶,而且时常与儿子一道玩分茶游戏。正如《疏山东堂昼眠》诗云:“香缕萦檐断,松风逼枕寒。吾儿解原梦,为我转云团。”其实,陆游玩分茶的主要原因是官场壮志未酬,雄图难展。年青时,他曾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雄心壮志。无奈于坎坷的仕途生涯,报国热情逐渐消退。晚年的陆游,虽然没有了济世之志,却能从“饭软茶甘”中得到满足。正如他自己所写道“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与此同时,他依旧心系武夷,情系建茶,直至终其天年。
后人评价:“陆游的建茶诗体性典雅、情致恳切、风骨趥劲,文采斐然,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如今,建茶已穿越千年仍香溢华夏,正可谓“建茶因陆游而名,陆游因建茶而雅”。陆游对茶叶特别是建茶的精神寄托,无疑也告诉我们一个人生哲理:品茶可以排遣寂寞,茶香可以驱赶苍凉。有此境界,陆游在宋代掀起了茶学诗文的最高潮,无愧于中国文坛中“茶圣”。